约翰·马克·科默(John Mark Comer)的著作《践行这道:与耶稣同在、效法耶稣、行他所行》(Practicing the Way: Be with Jesus. Become like Him. Do as He Did)被评为 ECPA 2025 年度基督教图书。许多福音派基督徒正在讨论书中对属灵生命塑造的构想,这并不出人意料。那么,我们是否需要更多地与科默的作品对话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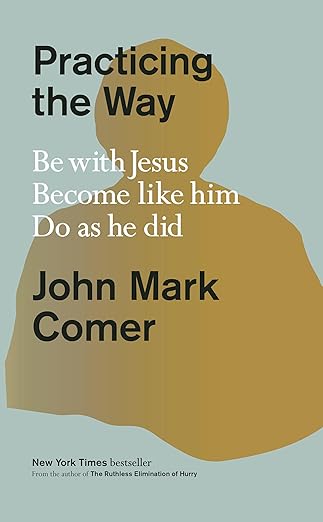 首先,人们对他的方法既充满兴趣又颇感不安,这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一些更深层的问题。我与不少基督徒交流,他们普遍觉得科默的灵性塑造方式有些不妥,却又说不清具体原因。这种张力值得我们认真进一步思考。
首先,人们对他的方法既充满兴趣又颇感不安,这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一些更深层的问题。我与不少基督徒交流,他们普遍觉得科默的灵性塑造方式有些不妥,却又说不清具体原因。这种张力值得我们认真进一步思考。
其次,科默的方法与改革宗理解的属灵塑造之间的差异确实值得探讨。科默的书影响了许多福音派人士,而福音派运动本身正是源自十八世纪复兴时期的改革宗传统。可惜我自己的那本讨论改革宗灵性塑造的书,因出版流程已进入后期阶段,无法直接与科默的观点展开对话。
这篇文章并不是一本书评。我真正想做的,是指出《践行这道》有三个关键之处偏离了宗教改革家(我认为圣经本身)所倡导的灵性塑造模式。
改革宗传统坚持:唯有因圣灵重生并与基督联合的人,其属灵生命才可能成长。脱离这种救赎性的联合,成长便无从谈起。因为惟有当我们“在基督耶稣里”,他才能成为我们的“公义和圣洁”(林前 1:30)。耶稣明确教导:“人若不重生,就不能见神的国”(约 3:3)。
然而,在《践行这道》中,重生和与基督联合的教义几乎完全缺席。科默确实谈到圣灵的重要性,并说属灵塑造需要你“藉着圣灵安居在耶稣的同在中”(37 页)。但他并没有解释人如何得到圣灵的帮助;在书中也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,圣灵使人重生是一个清晰而决定性的时刻,而正是借着这个时刻,神“重生了我们,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”(彼前 1:3)。
相反,科默把焦点放在成为耶稣的“学徒”上,把他视为最伟大的拉比,目标是成为一个能“说耶稣所说、行耶稣所行的那类人”(122 页)。这样的描述虽以耶稣为中心值得肯定,却忽略了圣灵促成的我们与基督的联合。科默的整套方法基本上围绕着:耶稣在地上的事奉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可效法的榜样。效法基督确实是一条明确的圣经主题(如彼前 2:21),但在理解基督是谁、以及他所成就的一切时,这并不是全部,更不是最重要的主题。
当我们过度强调“耶稣作为榜样”这个主题时,便会遮蔽一个圣经真理:我们首要的、根本的需要不是道德导师,而是救主。圣经教导说,“凡信耶稣是基督的,都是从神而生”(约壹 5:1)。这意味着,没有“从神而生”的人,根本无法相信耶稣是基督,也就不可能在属灵生命上有任何成长。比如,甘地虽然从耶稣的道德榜样中得到启发,但显然他从未悔改归信,最终仍然死在罪中。
宗教改革的核心,正是要恢复“以神的话语为中心”的敬虔生活。改教家们坚信,唯有不断深入研读神的话语,才能真正推动灵命成长。他们也教导,任何灵命塑造的方式都必须源自圣经、倚靠圣经。正因如此,许多中世纪信徒习用的灵性塑造方法被舍弃,转而回归《诗篇》119:9 所启示的朴素真理:“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?是要遵行你的话。”
科默在《践行这道》中,将读经列为个人“生活准则”(Rule of Life)中必须纳入的九项核心操练之一(181 页)。他也写道,“圣经是我们‘藉着心意更新而改变’的主要途径”(186 页)。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?
首先,读经不该只是“耶稣门徒用来塑造灵性”的众多方法之一(181 页),而是我们与神相交的根本途径。正如神学家巴文克所说:“圣经是连接天国与尘世的永恒纽带。”
但科默却将“更多查考圣经”称为“注定失败的策略”,并认为“做礼拜、听精彩讲道、定期查经......在大规模群体中通常难以带来真正深刻的改变”(86-87 页)。他一方面肯定讲道和查经“不仅有益,更是必需”(86 页),另一方面又断言单靠这些“远远不足以”促进灵命成长(87 页)。
这种论调令人想起中世纪教会的做法——他们表面尊崇圣经,却在实际操练中认为神的话语不够用。当时教会主张,真正的灵命突破要靠各种附加的仪轨修行。但对秉承改革宗精神的基督徒而言,神的话语始终是我们敬虔生活的核心。圣经既是改变生命的根本动力,也是一切属灵成长的蓝图。
科默在《践行这道》中展现的神学立场兼容并蓄,导致神学立场不够清晰。他将神学传统迥异甚至彼此对立的著述混为一谈,却对其中的矛盾轻描淡写。虽然他偶尔也会引用改革宗的思想家如提摩太·凯勒(Tim Keller)、罗莎莉亚·巴特菲尔德(Rosaria Butterfield)、提姆·切斯特(Tim Chester),但他更多依赖的是天主教作家(圣女大德兰 [Teresa of Ávila]、依纳爵·罗耀拉 [Ignatius of Loyola]、卢云 [Henri Nouwen])、东正教作家(卡利斯托斯·维尔 [Kallistos Ware]、卡利斯托斯·卡塔菲吉奥蒂斯 [Kallistos Katafygiotis])、贵格会神秘主义者(托马斯·凯利 [Thomas Kelly]),甚至还有非基督徒灵性作者纪伯伦(Kahlil Gibran)。
他将这些背景各异的思想家统称为“耶稣之道的大师”(47 页),暗示这些“灵性大师”(43 页)虽然来自不同传统,却是殊途同归。这显然不符合事实。
比如他在书中引用天主教作家论及“圣体圣礼(Blessed Sacrament)”时,仅轻描淡写地提上一句“即新教徒所说的圣餐”(42 页)。然而对圣礼理解的根本分歧,正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核心争议。更讽刺的是,在同页他又引述贵格会凯利的观点,而这个流派恰恰以完全放弃外在圣餐仪式著称。科默从未提醒读者,这些“耶稣之道的大师”(43 页)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神学冲突。
这种兼收并蓄的后果,就是构建出一套在基督教历史上找不到确切渊源的灵性塑造体系。尤其值得玩味的是科默对东正教作家威尔《东正教之路》(The Orthodox Way)的推崇,科默写道:“我读这本精彩绝伦的书时,就仿佛回到了家”(237 页)。
但《践行这道》既没有东正教对圣像的崇敬,也缺乏对“天主之母”(Theotokos)马利亚的尊崇,更不见使徒统绪的祭司职分——而这些恰恰是东正教灵性塑造的支柱。如果他读《东正教之路》真有“回家”的感觉,那为何他没有加入东正教会?部分原因恐怕是:一旦他真正扎根于某个具体传统,他就无法继续维持自己这种自助餐式的灵性塑造模式了。
科默为基督徒生活勾勒的蓝图,本质上是一种“随意挑选”的自助餐式方法。这并不是指他暗地里是天主教或东正教的拥护者、却刻意隐瞒自己的立场,而是说这种模式缺乏稳固根基,难以融入任何既定的基督教传统。
与此相比,改革宗的灵命塑造强调完全、一致地以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。正是这种坚实的圣道根基,历经数世纪考验,始终保持着连贯性与生命力。
只要改革宗确实正确理解了圣经,《践行这道》在属灵塑造方面就代表了一种明显偏离圣经的方式。正如科默对“重生”和“与基督联合”主题的轻描淡写所显示的那样,只要属灵塑造不扎根于圣经,它就会随着时代中看似吸引人的各种神学潮流四处漂移。
就改革宗传统对圣经的正确理解而言,《践行这道》显然偏离了符合圣经的灵性塑造观。从科默淡化“重生”“与基督联合”等核心教义可以看出,一旦灵命塑造脱离圣经锚点,就难免随波逐流,追逐当下流行的神学风潮。
或许科默与其他一些人对福音派的宗教改革传统已经感到不满,想要彻底摆脱它。决定在他们手里。但如果真是这样,他们就应该清楚地说出来,并坦然承担这个选择的后果。
译:MV;校:JFX。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:The Problem with Comer’s Cafeteria Approach to Spirituality.